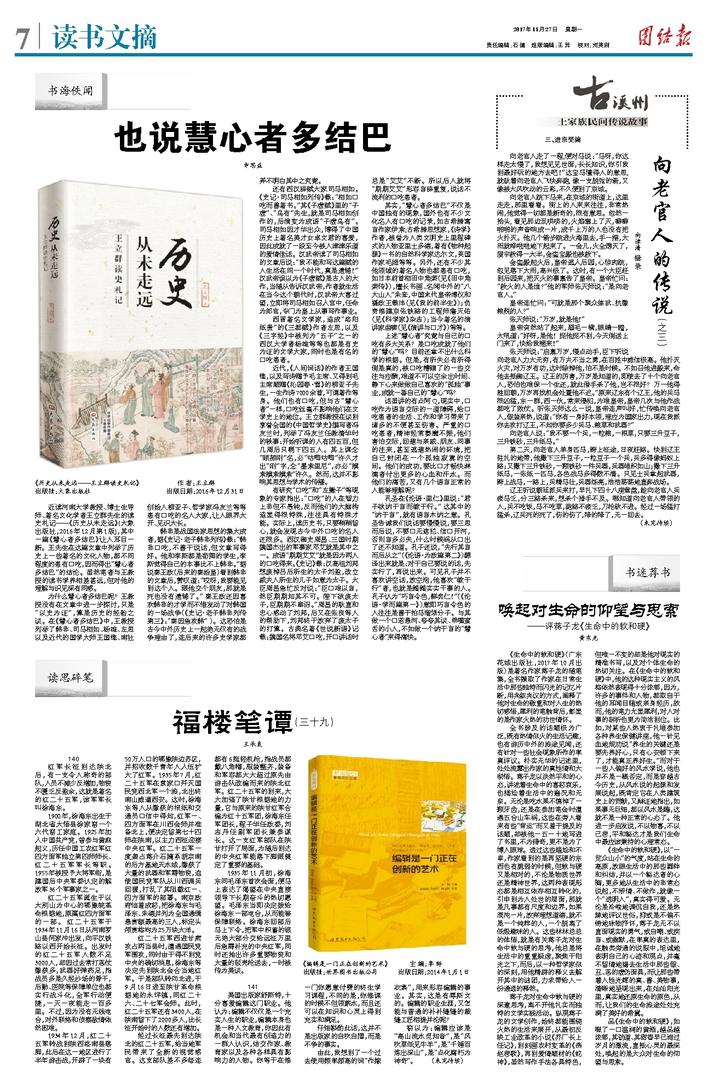申思益
近读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学者王立群先生的读史札记——《历史从未走远》(大象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其中一篇《慧心者多结巴》让人耳目一新。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物,都不同程度的患有口吃,因而得出“慧心者多结巴”的结论。虽然笔者与王教授的读书学养相差甚远,但对他的理解与识见深有同感。
为什么慧心者多结巴呢?王教授没有在文章中进一步探讨,只是“以史为证”,算是历史的经验之谈。在《慧心者多结巴》中,王教授列举了韩非、司马相如、杨雄、左思以及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南社创始人柳亚子、哲学家冯友兰等等患有口吃的名人大家,让人眼界大开、见识大长。
韩非是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口吃,不善于说话,但文章写得好。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觉得自己的本事比不上韩非。”据说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看到韩非的文章后,赞叹道:“哎呀,我要能见到这个人。跟他交个朋友,那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 秦王政还因喜欢韩非的才学而不惜发动了对韩国的一场战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秦因急攻韩” )。这恐怕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一起绝无仅有的战争理由了,连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弄不明白其中之究竟。
还有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其《子虚赋》里的“子虚”、“乌有”先生,就是司马相如创作的,后演变为成语“子虚乌有”。司马相如因才华出众,博得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美才女卓文君的喜爱,因此成就了一段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爱情佳话。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文章后说:“我不能和写这篇赋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遗憾!”汉武帝误以为《子虚赋》是古人的大作,当随从告诉汉武帝,作者就生活在当今这个朝代时,汉武帝大喜过望,立即将司马相如召入宫中,任命为郎官,专门为皇上从事写作事业。
西晋著名文学家,造成“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作者左思,以及《三字经》中被列为“五子”之一的西汉大学者杨雄等等也都是有史为证的文学大家,同时也是有名的口吃患者。
近代,《人间词话》的作者王国维,以及写诗赠予毛主席、又得到毛主席题赠《沁园春·雪》的柳亚子先生,一生作诗7000余首,可谓著作等身。他们也有口吃,但与古“慧心者”一样,口吃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王立群教授在谈到享誉全国的《中国哲学史》撰写者冯友兰时,列举了冯友兰任教清华时的轶事:开始听课的人有四五百,但几周后只剩下四五人。其上课念“顾颉刚”名,必“咕唧咕唧”许久才出“刚”字,念“墨索里尼”,亦必“摸索摸索摸索”许久。然而,这并不影响其思想与学术的传播。
有研究“口吃”和“左撇子”等现象的专家指出:“口吃”的人在智力上非但不愚钝,反而他们的大脑构造显得很特殊,往往具有特殊才能。实际上,读历史书,只要稍稍留心,就会发现古今中外口吃的名人还很多。西汉御史周昌、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军事家邓艾就是其中之一。成语“期期艾艾”就是因为两人的口吃得来。《史记》载:汉高祖刘邦想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周昌急忙反对说:“臣口难以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周昌的耿直和忠心感动了刘邦,后又在张良等人的帮助下,刘邦终于放弃了废太子的打算。古典名著《世说新语》记载:魏国名将邓艾口吃,开口讲话时总是“艾艾”不断。所以后人就将“期期艾艾”形容言辞重复,说话不流利的口吃患者。
其实,“慧心者多结巴”不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国外也有不少文化名人有口吃的记录,如古希腊寓言作家伊索;古希腊思想家,《诗学》作者,被誉为人类文明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著有《物种起源》一书的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英国作家毛姆等等。另外,还有不少其他领域的著名人物也都患有口吃,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见《田中角荣传》),擅长书画、名闻中外的“八大山人”朱耷,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和摄政王载沣(见《我的前半生》);负责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见《科学家》杂志);当今著名的演讲家曲啸(见《演讲与口才》)等等。
上述“慧心者”究竟与自己的口吃有多大关系?是口吃成就了他们的“慧心”吗?目前还拿不出什么科学的根据。但是,有所失必有所得倒是真的,被口吃糟蹋了的一些交往与应酬,难道不可以空余出时间、静下心来做做自己喜欢的“孤独”事业,成就一番自己的“慧心”吗?
话虽讲的有点阿Q,现实中,口吃作为语言交际的一道障碍,给口吃患者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了诸多的不便甚至伤害。严重的口吃患者,精神经常萎靡不振,他们害怕交际,回避与亲戚、朋友、同事的往来,甚至逃避热闹的环境,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寂寞的空间。他们的成功,要比口才畅快淋漓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而他们的痛苦,又有几个语言正常的人能够理解呢?
孔圣在《论语·里仁》里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其中的“讷于言”,就有语言木讷之意。孔圣告诫我们说话要慢慢说,要三思而后说,不要口无遮拦、信口开河,否则言多必失,什么时候祸从口出了还不知道。孔子还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篇第二》)翻译出来就是:对于自己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可见孔子并不喜欢讲空话,放空炮,他喜欢“敏于行”者,也就是踏踏实实干事的人。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篇第一》)意即巧言令色的人往往是善于拍马溜须分子。与其做一个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乖嘴蜜舌的小人,不如做一个讷于言的“慧心者”来得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