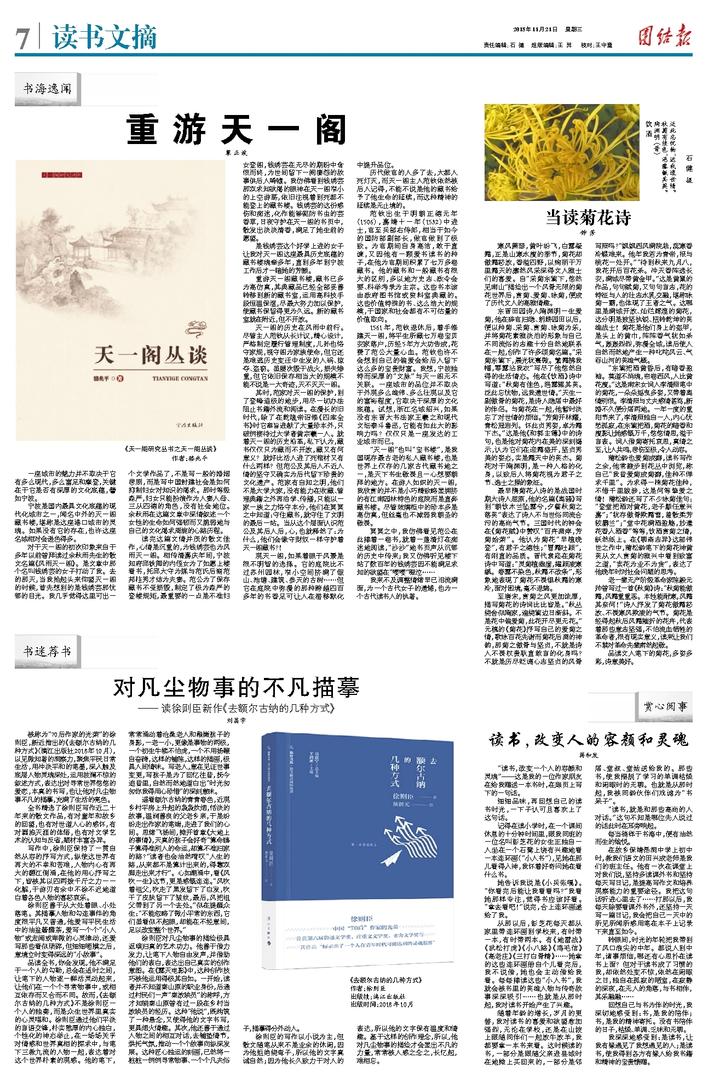覃正波
一座城市的魅力并不取决于它有多么现代,多么富足和摩登,关键在于它是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譬如宁波。
宁波是国内最具文化底蕴的现代化城市之一,闻名中外的天一阁藏书楼,堪称是这座港口城市的灵魂。如果没有它的存在,也许这座名城相对会逊色得多。
对于天一阁的初次印象来自于多年以前曾拜读过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名篇《风雨天一阁》。是文章中那个名叫钱绣芸的女子打动了我。去的那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中国封建社会是如何抑制妇女对知识的渴求。那时等级森严,妇女只能扮演作为人妻人母、三从四德的角色,没有社会地位。余秋雨在这篇文章中深情叙述一个女性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的心路历程。
读完这篇文情并茂的散文佳作,心情是沉重的,为钱绣芸也为风雨天一阁。相传清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卿的内侄女为了如愿上楼看书,托邱大守为媒与范氏后裔范邦柱秀才结为夫妻。范公为了保存藏书不受损毁,制定了极为森严的登楼规矩,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准妇女登阁,钱绣芸在无尽的期盼中含恨而终,为世间留下一阙凄怨的故事供后人唏嘘。我仿佛看到钱绣芸那双求知欲渴的眼神在天一阁窄小的上空游荡,依旧注视着到死都不能登上的藏书楼。钱绣芸的这份感伤和痴迷,化作能够驱防书虫的芸香草,日夜守护在天一阁的书页中,散发出淡淡清香,满足了她生前的愿望。
是钱绣芸这个好学上进的女子让我对天一阁这座最具历史底蕴的藏书楼魂牵多年,直到多年到宁波工作后才一睹她的芳颜。
重游天一阁藏书楼,藏书已多为高仿真,其典藏品已经全部妥善转移到新的藏书室,运用高科技手段恒温保湿,尽最大努力加以保护,使藏书保留得更为久远。新的藏书室就在附近,但不开放。
天一阁的历史在风雨中前行。尽管主人范钦从长计议,精心设计,严格制定履行管理制度,儿孙也恪守家规,视守阁为家族使命,但它还是难逃历史变迁中生发的人祸、掠夺、盗窃。虽屡次毁于战火,损失惨重,但它依旧保存相当大的规模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天不灭天一阁。
其时,范家对天一阁的保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书籍外流和阅读。在漫长的旧时代,除了在乾隆帝诏修《四库全书》时它奉旨进献了大量珍本外,只破例接待过大学者黄宗羲一人。就着天一阁的历史沿革,私下认为,藏书仅仅只为藏而不开放,藏又有何意义?就好比活人进了死棺材又有什么两样?但范公及其后人不近人情的坚守又确实为后代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范家有自知之明,他们不是大学大家,没有能力在收藏、管理典籍之外再治学、传播,只能以一家一族之力恪守本分,他们在冥冥之中知道:守住藏书,就守住了文明的最后一站。当从这个层面认识范公及其后人后,心,也就释然了:为什么,他们会像守财奴一样守护着天一阁藏书?!
观天一阁,如果着眼于风景是很不明智的选择。它的庭院比不过苏州园林,窄小空间挤满了假山、池塘、建筑、参天的古树……但它在庭院中弥漫的那种跨越四百多年的书香足可让人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品位。
历代做官的人多了去,大都人死灯灭,而天一阁主人范钦依然被后人记得,不能不说是他的藏书给予了他生命的延续,而这种精神的延续是无止境的。
范钦出生于明朝正德元年(1506),嘉靖十一年(1532)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副部长,做官做到了极致。为官期间自身高洁,敢于直谏,又因他有一颗爱书读书的种子,在他为官期间积累了七万多卷藏书。他的藏书和一般藏书有很大的区别,多以地方史志、政令会要、科举考录为主宗。这些书本该由政府图书馆或资料室典藏的。这些价值特殊的书、这么浩大的规模,于国家和社会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取向。
1561年,范钦退休后,着手修建天一阁,将平生所藏七万卷宝贝安家落户,历经5年方大功告成,花费了范公大量心血。范钦也许不会想到自己的偏爱会给后人留下这么多的宝贵财富。我想,宁波独特而深厚的“文脉”与天一阁无不关联。一座城市的品位并不取决于外观多么雄伟、多么壮观以及它的富裕程度,它取决于深厚的文化底蕴。试想,浙江名城绍兴,如果没有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现代文坛泰斗鲁迅,它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吗?仅仅只是一座发达的工业城市而已。
“天一阁”也叫“宝书楼”,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仅存的几家古代藏书地之一,是天下书生敬畏且一心想要朝拜的地方。在游人如织的天一阁,我欣赏的并不是小巧精致略显拥挤的有江南园林特色的庭院而是直奔藏书楼。尽管玻璃柜中的珍本多是高仿真,但丝毫也不减弱我朝圣的敬畏。
冥冥之中,我仿佛看见范公在此捧着一卷书,就着一盏清灯在痴迷地阅读,“沙沙”地书页声从沉郁的历史中传来;我又仿佛听见楼下站了数百年的钱绣芸因不能满足求知的欲望在“嘤嘤”啜泣……
我来不及调整情绪早已泪流满面,为一个古代女子的遗憾,也为一个古代读书人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