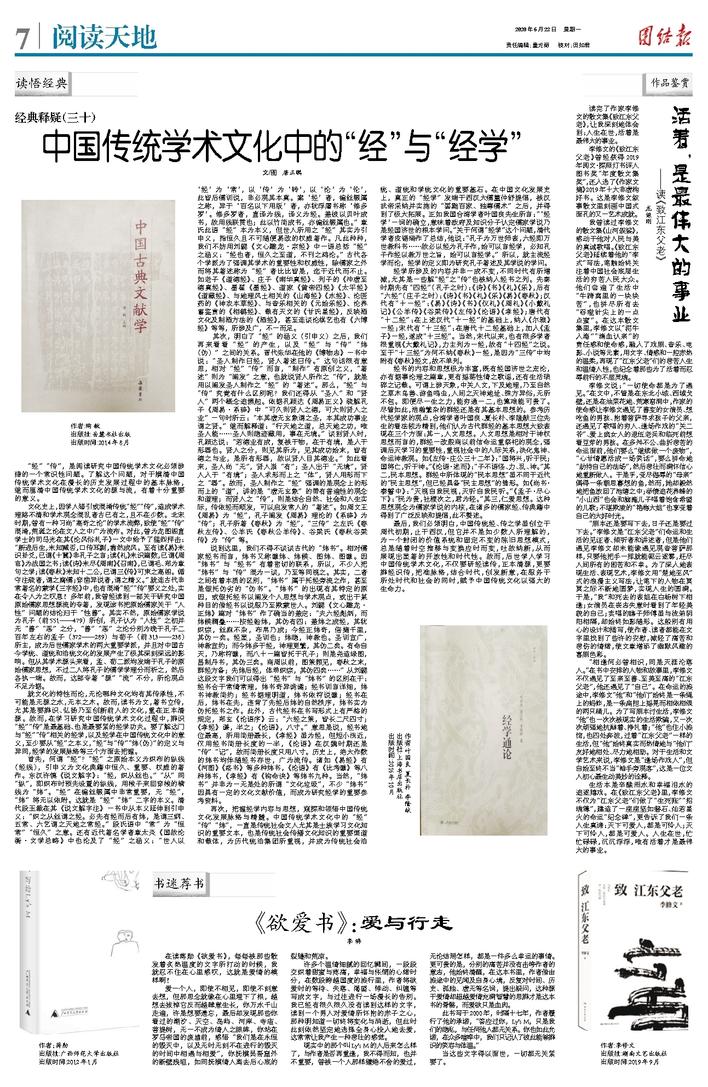文/图 唐正鹏
“经”“传”,是阅读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必须涉猎的一个常识性问题。了解这个问题,对于摸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脉络,继而厘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源与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史上,因学人错引或混淆传统“经”“传”,造成学术理路不清和学术观念混乱者古已有之,且不在少数。北宋时期,曾有一种习尚“高奇之论”的学术流弊,致使“经”“传”混淆,荒诞之论在文人之中广为流布。对此,曾为龙图阁直学士的司马光在其《论风俗札子》一文中给予了猛烈抨击:“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异说者,谓之精义。” 就连古代非常著名的蒙学《三字经》中,也有混淆“经”“传”要义之处,实在令人为之叹息!多年前,我曾经读到一部关于研究中国原始儒家思想源流的专著,发现该书把原始儒家关于“人性”问题的结论归于“性善”。其实不然,原始儒家学说为孔子(前551——479)所创,孔子认为“人性”之初并无“善”“恶”之分,“善”“恶”之论分别为晚于孔子二百年左右的孟子(372——289)与荀子(前313——238)所主,成为后世儒家学术的两大重要学派,并且对中国古今学统、道统和治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深远的影响。但从其学术源头来看,孟、荀二派均发端于孔子的原始儒家思想,不过二人将孔子的儒学学理分而析之,然后各执一端。故而,这部专著“源”“流”不分,所论观点不足为据。
就文化的特性而论,无论哪种文化均有其传承性,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而,读书为文,著书立传,尤其是要辨识、弘扬乃至创新前人的文化,重在正本清源。故而,在学习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过程中,辨识“经”“传”是最基础、也是最要紧的经学功夫。要了解这门与“经”“传”相关的经学,以及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至少要从“经”之本义,“经”与“传”“纬(伪)”的定义与异同,经学的发展脉络等三个方面去把握。
首先,何谓“经”?“经”之原始本义为织布的纵线(经线),引申义为文化典籍中恒久、重要、权威的著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经,织从丝也。”“从”同“纵”,即织布时预先设置的纵线,用梭子来回穿梭的横线为“纬”。“经”在编丝缀属中非常重要,无“经”,“纬”将无以依附。这就是“经”“纬”二字的本义。清代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一书中从本义延伸到引申义:“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谓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段氏语中“常”为“恒常”“恒久”之意。还有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也论及了“经”之涵义:“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观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章氏此语“经”本为本义,但世人所用之“经”其实为引申义,指恒久且不可随便易改的权威著作。凡此种种,我们不妨用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中一语总括“经”之涵义:“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古代各个学派为了强调其学术的重要性和权威性,除儒家之外而将其著述称为“经”者比比皆是,迄于近代而不止。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真经》、列子的《冲虚至德真经》、墨翟《墨经》、道家《黄帝四经》《太平经》《道藏经》、与地理风土相关的《山海经》《水经》、论医药的《神农本草经》、与音乐相关的《元始乐经》、论养蓄鉴赏的《相鹤经》、载有天文的《甘氏星经》,反映酒文化及制酒方法的《酒经》,甚至连谈论棋艺也有《六博经》等等,所涉及广,不一而足。
其次,明白了“经”的涵义(引申义)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经”的产生,以及“经”与“传”“纬(伪)”之间的关系。晋代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一书中说:“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这句话很有意思,相对“经”“传”而言,“制作”有原创之义,“著述”则为“阐发”之意,也就说贤人所作之“传”,就是用以阐发圣人制作之“经”的“著述”。那么,“经”与“传”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还得从“圣人”和“贤人”两个概念追溯起。依据孔颖达《周易正义》疏解孔子《周易·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一句时所云:“本其虚无玄象谓之圣,本其成功事业谓之贤。”继而解释道:“行天地之道,总天地之功,唯圣人能……圣人则隐迹藏用,事在无境。”谈到贤人时,孔颖达说:“若德业有成,复被于物,在于有境,是入于形器也。贤人之分,则见其所为,见其成功始末,皆有德之与业,是所有形器,故以贤人目其德业。”如此看来,圣人尚“无”,贤人崇“有”;圣人出于“无境”,贤人入于“有境”;圣人求形而上之“体”,贤人用形而下之“器”。故而,圣人制作之“经”强调的是观念上的形而上的“道”,讲的是“虚无玄象”的带有普遍性的观念和道理;而贤人之“传”,则是结合自然、社会和人生实际,传依经而顺发,可以启发常人的“著述”。如周文王《周易》为“经”,孔子阐发《周易》理论的《系辞》为“传”;孔子所著《春秋》为“经”,“三传”之左氏《春秋左传》、公羊氏《春秋公羊传》、谷梁氏《春秋谷梁传》为“传”等。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古代的“纬书”。相对儒家经书而言,纬书又称谶纬、纬候、图纬、图谶。因“纬书”与“经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不少人把“纬书”与“传”混为一谈,乃至等同视之。其实,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纬书”属于托经旁流之作,甚至是假托伪劣的“伪书”。“纬书”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原因,或假托经书以阐发个人思想与学术观点,或出于某种目的借经书以说服乃至欺蒙世人。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对“纬书”作了确当的盖定:“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策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从刘勰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得出“经书”与“纬书”的区别在于:经书合于常情常理,纬书奇异诡谲;经书训言详细,纬书神教简约;经书据理明道,纬书依符说谶;经书在后,纬书在先,违背了先经后纬的自然秩序,纬书实为伪托经书之作。此外,古代经书在书写形式上有严格的规定,郑玄《论语序》云:“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意思是说,经书地位最高,所用简册最长,《孝经》虽为经,但短小浅近,仅用经书简册长度的一半,《论语》在汉魏时期还是“传”“记”,故而简册长度只用八寸。历史上,绝大作数的纬书均伴随经书存世,广为流传。诸如《易经》有《河图》《洛书》等多种纬书,《论语》有《比考谶》等八种纬书,《孝经》有《钩命诀》等纬书九种。当然,“纬书”并非为一无是处的所谓“文化垃圾”,不少“纬书”因具有一定的文化文献价值,而成为研究经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再次,把握经学内容与思想,窥探和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与精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传”“纬”,一直是传统社会文人尤其是士族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文本,也是传统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和载体,为历代统治集团所重视,并成为传统社会治统、道统和学统文化的重要基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真正的“经学”发端于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倡,被汉武帝采纳并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并得到了极大拓展。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叶国良先生所言:“‘经学’一词的确立,意味着政府及知识分子认定儒家学说乃是经国济世的根本学问。”关于何谓“经学”这个问题,清代学者皮锡瑞作了总结,他说:“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所以,就主流经学而论,经学的定义即为研究孔子著述及其学说的学问。
经学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代有所增减,尤其是一些解“经”之“传”也被纳入经书之列。先秦时期先有“四经”(孔子之时):《诗》《书》《礼》《乐》,后有“六经”(庄子之时):《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有“十一经”:《易》《诗》《书》《仪礼》《周礼》《小戴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孝经》;唐代有“十二经”:在上述汉代“十一经”的基础上,纳入《尔雅》一经;宋代有“十三经”:在唐代十二经基础上,加入《孟子》一经,遂成“十三经”。当然,宋代以来,也有很多学者很重视《大戴礼记》,力主列为一经,故有“十四经”之说。至于“十三经”为何不纳《春秋》一经,是因为“三传”中均附有《春秋》经文,故不单列。
经书的内容和思想极为丰富,既有经国济世之宏论,亦有据事论理之篇章,更有摇荡性情之歌谣,还有生活琐碎之记载。可谓上涉天象,中关人文,下及地理,乃至自然之草木鸟兽、游鱼鸣虫,人间之天神地址、殊方异俗,无所不包。即便尽一生之力,能穷通一二,也算难能可贵了。尽管如此,浩瀚繁杂的群经还是有其基本思想的。参考历代经学家的观点,台湾学者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三位先生的看法较为精到,他们认为古代群经的基本思想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文思想。人文思想是相对于神权思想而言的,群经一改殷商以前信命运重祭祀的观念,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重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淡化鬼神、命运神教观。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其二,民本思想。群经中所体现的“民本思想”虽不同于近代的“民主思想”,但已经具备“民主思想”的雏形。如《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三,仁爱思想。这种思想观念为儒家学说的内核,在诸多的儒家经、传典籍中得到了广泛反映和提倡,此不赘述。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传统经、传之学虽创立于周代初期,止于西汉,但它并不是如少数人所理解的,为一个封闭的价值系统和固定不变的陈旧思想模式,总是随着时空推移与变换应时而变,吐故纳新,从而展现出显著的开放性和时代性。故而,后世学人学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不仅要研经读传,正本清源,更要辨经识传,把准脉络,结合时代,创发新意,在服务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同时,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