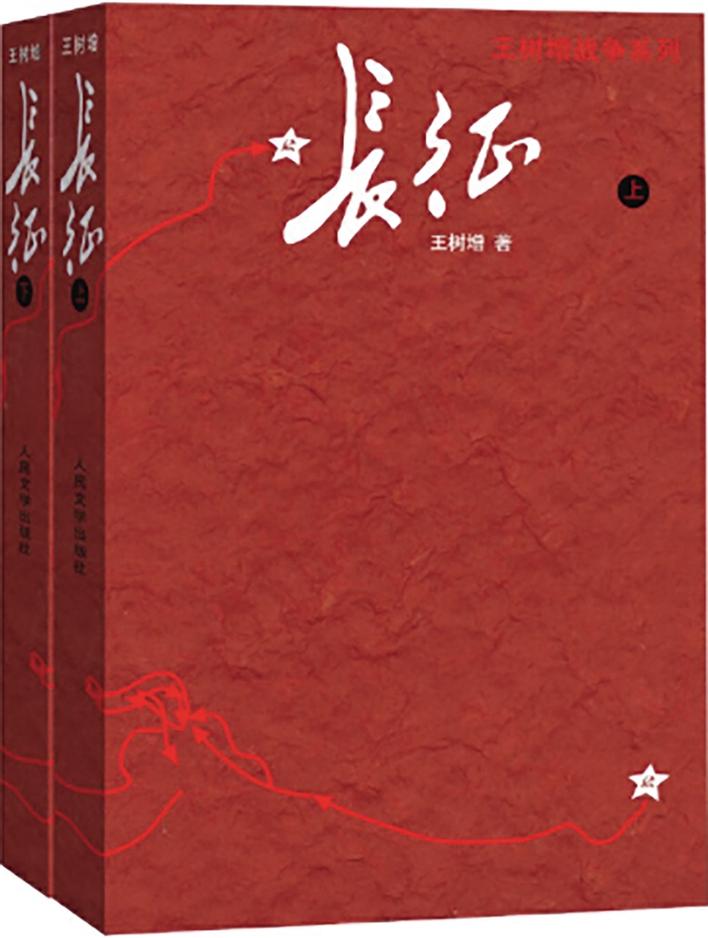张正望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毛泽东
记不清是十年前的哪些个夜晚,我在灯下彻夜不眠地读完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创作的《长征》一书。十年后的今天,我又重读他这部修订版的《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那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以无与伦比的勇敢付出的巨大牺牲,依然令人心潮澎湃,神思飞扬,热泪盈眶。
从公元一○○○年至公元二○○○年的千年间,作为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事件——长征,王树增在他的这部全景而深入地揭示长征始末的纪实性文学巨著中,是这样为读者拉开序幕的:“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这支萧克率领的作为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他们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到国民党军重兵突袭。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局势日益恶化,六军团必须撤出井冈山根据地,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要求把一切都带走。“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其中还有十名女性,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磨面机。”他们带着这些辎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英勇突围,用红军战士坚强的斗志和超常的毅力,证明蒋介石的碉堡、飞机、大炮和穷凶极恶的追杀无法阻挡红军朝着胜利前进的脚步。
作者在书的第十章《残阳如血》中,详尽地书写了红军在赤水河两岸、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缝隙中来回穿越的惊心动魄的过程,每一次渡河,无不令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至今依旧有人说,如果将红军在贵州的转战路线一一画出将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因为那些对红军来讲生死仅在一瞬间的行走路线像是拆乱了的线团难以理出头绪。这一以追逐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敌对双方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和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四渡赤水”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作者精彩的文字叙述把用兵如神的毛泽东高超的战争艺术完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后令人在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洗礼中,生发出对领袖和红军将士们的崇敬和爱戴。
阅读中,我能时时感受到一种来自人类崇高的、令人激越的精神力量的鼓舞。对于红军将士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播种下去,然后渴望着收获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意放弃的梦想。“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从红军领袖,到各级将领,再到普通一兵;从革命勋臣,到巾帼英雄,再到阳光少年,作为红军长征的参与者,他们用最坚强的人类意志,架构起最雄伟最坚固的信仰长城。朱德,红军的总司令,作家用深厚的笔力,再现了朱老总英勇的形象。“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受到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参加南昌起义的所有部队由两万人锐减不到两千人,面对严峻形势,为保存干部,起义军被迫决定解散组织,撤离部队。在革命危急关头,时任第九军军长朱德这时站了出来,并讲出了他一生中那句著名的话:“不愿意继续奋斗的,可以走;继续革命的留下,我是要继续革命的。”留下的人数大约是八百,在这些“愿意继续奋斗”的青年中,有26岁的陈毅。有了这次坚定信仰的表达,有了这次军队力量的保存,我们就可以理解,在长征这场考验人心灵与身体的战争中,朱德是怎样用具有号召力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
书中细腻地描写了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之间的革命友谊和信任。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各自带着他们人数不多的部队在宁冈县的砻市相见了,这就是后来中国革命史中所说的“井冈山会师”。 两军会师后,合编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政治友谊,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坚固无比的革命情谊的典范。毛泽东曾经说过:“朱毛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家庭出身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差别的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意味深长的关系。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那就是:无论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背得如何流畅,毕竟马克思和列宁从没有来过中国,他们所有的革命理论都产生于欧洲的人文历史中,而中国有现实的、具体的、独特的国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公认的行家里手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而是毛泽东。因此,即使在毛泽东受到排斥和冷落的时候,周恩来也会把党内的重要文件送请毛泽东过目,就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请教毛泽东。他甚至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给予毛泽东细致的照顾,包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警卫安全乃至食品和香烟的供应。如果仅从信任的角度讲,面对能够滔滔不绝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经典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周恩来更倾向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熟读了《水浒传》的毛泽东。当周恩来认准了这一点之后,这个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温文尔雅的革命家,以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