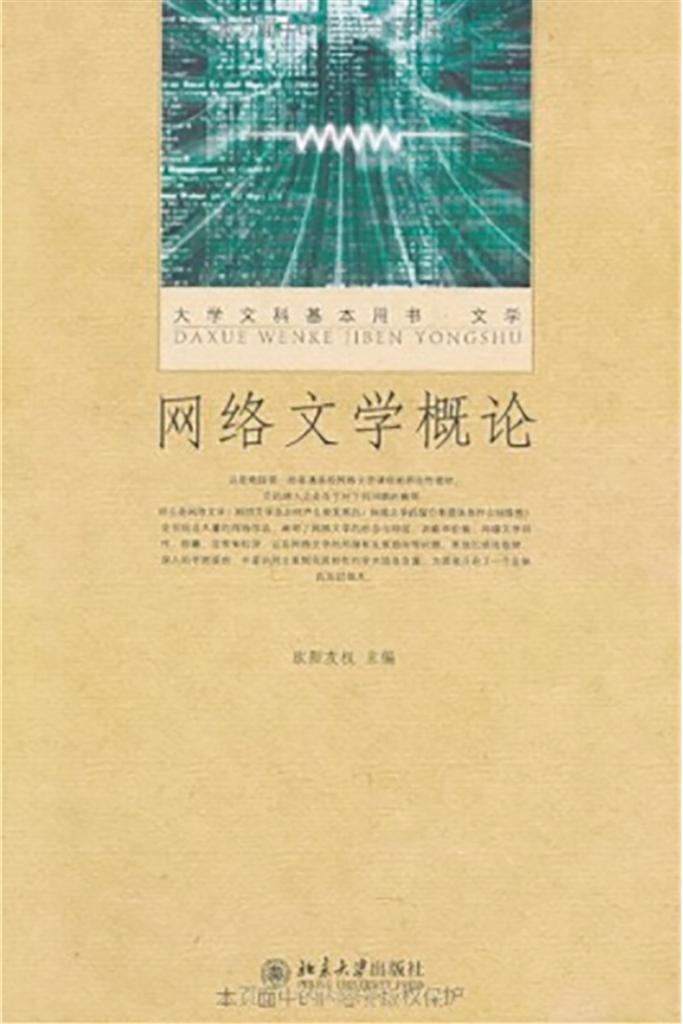石 健
2018年10月20日
网络文学江湖·白日梦工厂
今天的主讲是欧阳友权老师。他是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我读文艺学研究生时,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报纸副刊在网络兴起之后的境遇研究,所以,我曾认真阅读过他的著作《网络文学论纲》和《网络文学概论》。
尤其是后一本书,虽为概论,被高校采用为教材,但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教材。乃至看完之后,意犹未尽,心中感慨:原来,教材可以这样诗意盎然地进行研讨、可以这样天马行空地进行书写!
欧阳友权老师完全是把网络文学的世界当成一个江湖来书写的,虽然其中有数据、图表之类分析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以及理性的反思,但他在行文当中,不把自己当冷眼的旁观者,而是幻化为其中一员,设身处地,与网络写手们感同身受,书写他们的奋斗和挣扎,传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在欧阳老师的眼中笔下,网络是一个江湖,网络写手们则是江湖游侠。他们隐姓埋名,仗剑前行,不逐庙堂之上权与利,但求江湖之中有声名。但江湖风云,变幻莫测,风雨兼程,几多悲辛,几多无奈,令人感慨。
欧阳老师的文笔非常好,哪怕是研究性理论专著,读来也快意,有余兴,引人深思。
11年前,《网络文学概论》是最令我脑洞大开的教材。原来,学问是不必板着脸孔的,是可以做得有趣的。有趣了才有意思、有意义。此一文学研究令我们得以正视上世纪90年代网络兴起后文学的种种嬗变,对种种激荡摆正心态,不必太过惊慌太过不安。当然,这些已成过去。
人们已经开始慢慢习惯网络时代文学媒介和载体的变化,这其中包括文学文本形式、创作模式、传播方式等多方面的转变……人们在网络文学面前变得镇定,因为文学有万变不离其宗、万古不变的核心要义。当然,我是指那些最优秀的文字或是最用心的文字。
在毛十七的同班同学里,我认识了三位网络作家:马强志、宋春波、王瑶。他们都是小青年,小到有1996年出生的。他们是职业作家,很有思想,靠码字养家,很勤奋。
他们值得我们这些以文字娱乐或娱乐文字的体制内的中年人学习。与他们同窗,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亦有只争朝夕的强烈冲动。
我开始感受到毛院将传统作家与网络作家混合教学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刺激。它把不同年龄、不同成就的写作者安排在同一场域之内,利用同一时空的交互碰撞,以优秀者刺激后进者,进而激励后者的写作冲动和写作斗志。
所以,当那天我斗志昂扬地对帅气的马强志说:“我回家要向你学习,每天写很多。”听闻此言,马强志哈哈大笑,说:“姐姐,你知道吗?写散文和写小说是不同的。散文灵感很重要,不可能随时都有的,小说则朝着既定方向和构架走就可以了。”
80后小青年马强志情商很高,没说我在做白日梦,我在内心十分感谢他,但我也不为我放诞的言语后悔。每个爱好文学的人都是白日梦患者,而毛院则是纵容我们做梦的地方。
2018年10月28日
一言一行总关情
我很少主动加他人微信,这个世界,现实太喧嚣,网络也聒噪。人到中年,越发觉得朋友难觅,而书本才是知心人。
但是,听到马强志在一次文学课的交流环节发言后,我主动加了这个80后网络作家的微信。他针对前一位同学所表达的“经济效益是衡量文学作品优秀与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的观点,勇敢地站出来说了真话。
马强志结合当下种种文学现象的正负面影响、自身的阅读与网络文学创作实践,正色道:“撇开大道理不说,如果我们的创作只顾经济效益,以色情、暴力谋求人气、眼球和钱财,毫不顾及下一代的成长,势必造成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如此,我们根本不配为人父母,又如何担当作家神圣的社会责任?”
这位小青年后来被我称呼为“小马哥”。那天,他短短的发言有礼有节,有理有据,声音温和、语调平和,但始终都包裹着义正与词严。他的言论从毛泽东文学院小礼堂的角落里冒出来,有如在平静的水面抛下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荡出很远。
我坐在前排,离他并不远,但因为数排人身的隔离,又觉得十分远。尽管如此,我还是屏息凝神地听到了他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并且确切地感受到了他在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激荡。
我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羞愧着,一边激动着。
很多时候,在公理与道义面前,全世界都会沉默,其中,有些人是根本不懂这些公义的,麻木冷漠、视而不见也就成了理所当然;有些人懂得,却不知怎么表达、辩驳、维护;也有的人深深明白,却碍于种种原因不说,以沉稳和成熟的名义遮盖世故与油滑,以缄默求得安稳或是利益。
我羞愧,因为自己第二、三点兼而有之。
我激动,因为遇见了小马哥这样世间难得的独立思考与品性纯直之人。
小马哥的发言掷地有声,令在场80余人同时沉默。话音落下后,全场仍然保持了数秒钟的静穆,空气与时间都有凝结的感觉。我第一个为他鼓掌,掌声接连响起,瞬即热烈地连成一片。小马哥所行所言,让我觉得公理和道义自在人心,永在人心,由此,内心又升腾起一些信念并且蓄积了一些力量。
小马哥的笔名叫“一桶布丁”,这与要么炫目、要么诗意、要么玄奥,总之是名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络作家笔名相差甚远。但认识并熟悉小马哥之后,觉得有着童真童趣的“一桶布丁”与之是协和匹配的。
我找到了小马哥这样的文友,也找到了聊天的对手。
一天课余聊天,我们共同聊到了《废都》和《金瓶梅》。巧合的是,我们都是在初中时代看的这两本书,而且,对其印象深刻的细节也惊人一致。尤其是谈及《金瓶梅》中的那颗葡萄,还有读《废都》时少男少女即触即通的一些情绪,我俩笑翻了。笑过之后,小马哥很严肃地说:“《金瓶梅》是很伟大的一部作品。”对此,我深以为然。
又一次课余,我叹口气,对小马哥说极羡慕网络小说作家们一天至少三五千字、多则万字的写作速度。听闻此言,他哈哈大笑,然后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安慰并解释:“石姐姐,散文创作与小说创作根本就是两回事。小说拟好提纲后,可以尽情想象、自由铺排。尤其是网络小说作家,迫于维持生计和读者阅读的压力,速度自然很快;但散文创作,除了考验读书的底子外,也很讲究文笔、布局、情绪,所以散文创作是没有网络小说创作来得自由的,也就需要时间来细磨慢碾。”
在毛泽东文学院学习的短短二十天里,小马哥和我常聊及读书,也偶尔提及我之前完全陌生的网络创作和网络作家。这是一种高度职业化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群体:每部作品都要预先形成完整详尽的写作提纲、目录、计划;有时,同时开写数部作品,每天都要写数千到万字;晚上熬夜加班成为常态;没有网站签约、不能维持一定浏览量,必然会影响到收入和生计……
确实,来毛泽东文学院学习,刨去白天上课、晚间交流的时间,一天时光所剩无多。在我们这类非职业写作者酣然入梦之时,小马哥是要熬夜创作更新作品的。
网络时代,人人都是写手。网络作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浩大的文学创作主力军。可是,任网络如何海量与包容,那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像唐家三少那样动辄上亿版税的网络作家,毕竟只是金字尖的那一个。作为依靠互联网发表文学作品的撰稿人,小马哥在这个信息爆炸、热点易燃易灭的时代,选择了这条生存之路,艰难可想而知。可创作,从来都不是轻松的活儿,也不是娱乐的话题;而有的人,是天生为写作而生的。喜欢喝酒、聊天、交友的小马哥表面过得热闹,但眼神里的小忧郁、偶尔的心事重重状,还有在聊天时透露出的阅读经历、以创作为乐的多年坚持、较成功的网络文学作品,让我觉得他就是为写作而生的。
小马哥的写作模式和写作状态同时也启发了我。写作者,哪怕是业余的,其实也应该有创作计划和创作纪律,找到自己喜欢并且适合的目标和方向,并以坚持和自律实现关于文学的一些梦想和企图。随性、松懈、怠惰,写作的版图将止于零碎散乱。
我反复约小马哥来湘西玩。湘西的山水风物,他应该喜欢,还有,湘西的路边摊也很适合他喝酒、消夜。
毛泽东文学院的学习经历过去了两年,那个集体太大、人数太多、三观繁复,其中人事感觉就要遗忘殆尽了,但我仍然不时想起小马哥——马强志,这个以“一桶布丁”为名在网络上发布小说作品的80后小青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