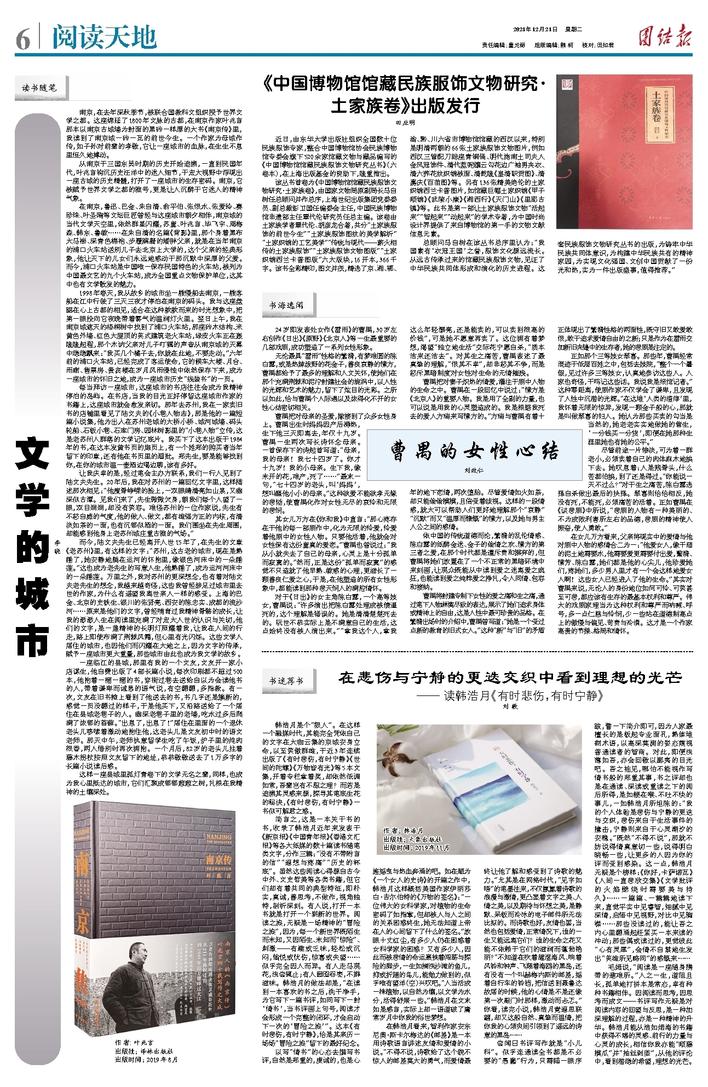刘效仁
24岁即发表处女作《雷雨》的曹禺,30岁左右创作《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生最重要的几部戏剧,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
无论最具“雷雨”性格的繁漪,有梦难圆的陈白露,或是热辣泼野的花金子,善良哀静的愫方,曹禺都给予了最多的理解和人文关怀,使她们在那个充满荆棘和泥泞封建社会的旋涡中,以人性的光辉和艺术的魅力,留下了炫目的光彩。之所以如此,恰与曹禺个人际遇以及浓得化不开的女性心结密切相关。
曹禺把对母亲的圣爱,嫁接到了众多女性身上。曹禺出生时妈妈因产后褥热,生下他三天即离去,年仅十九岁。曹禺一生两次写长诗怀念母亲。一首保存下的诗起首写道:“母亲,我的母亲!我七十四岁了。你才十九岁!我的小母亲。生下我,像未开的花,难产,死了……”最末一句,“七十四岁的老头,叫‘妈妈’,想叫醒他小小的母亲。”这种欲爱不能欲孝无缘的悲恸,使曹禺化作对女性无尽的哀怜和无限的悲悯。
其女儿万方在《你和我》中直言:“那心疼存在于他的每一部剧作中,化为无限的怜爱,怜爱着他剧中的女性人物。只要他活着,他就会对女性保有这份童真的爱恋。”曹禺也曾说过:“我从小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然而,正是这份“孤单而寂寞”的感觉不只造就了他早熟、敏感的心理,更滋长了一颗善良仁爱之心,于是,在他塑造的所有女性形象中,都能读到那种悲天悯人的满腔情怀。
对于《日出》的女主角陈白露,一个高等妓女,曹禺说:“许多演出把陈白露处理成被债逼死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她是清清楚楚死去的。玩世不恭实际上是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这点始终没有被人演出来。”“拿我这个人,拿我这么年轻漂亮,还是能卖的,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可是她不愿意再卖了。这位拥有着梦想,渴望“独立地生活”交际花宁愿自杀,“质本洁来还洁去”。对其生之痛苦,曹禺表述了最真挚的理解,“恨其不幸”,却非怒其不争,而是怒斥黑暗制度对女性对生命的无情摧残。
曹禺把对妻子炽热的情爱,灌注于剧中人物的生命之中。曹禺在一段回忆中说过:“愫方是《北京人》的重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方瑞与曹禺有着十年的地下恋情,两次堕胎。尽管爱情如火如荼,却只能偷偷摸摸,且倍受着歧视。这样的一段情感,就大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那个“哀静”“沉默”而又“温厚而慷慨”的愫方,以及她与男主人公之间的感情。
依中国的传统道德而论,繁漪的乱伦情感、陈白露的纸醉金迷、金子的偷情之欢、愫方的第三者之爱,在那个时代都是遭斥责和摒弃的,但曹禺将她们放置在了一个不正常的黑暗环境中来刻画,让观众既能从中读到爱之迷离爱之疯狂,也能读到爱之纯粹爱之挣扎,令人同情、包容和接纳。
曹禺将封建专制下女性的爱之痛和生之痛,通过笔下人物淋漓尽致的表达,展示了她们追求身体或精神上的自由,这是人性中最可珍贵的品格。在繁漪出场时的介绍中,曹禺曾写道:“她是一个受过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这种“新”与“旧”的矛盾正体现出了繁漪性格的两面性,既守旧又敢爱敢恨,敢于追求爱情自由的之新;只是作为在雷雨交加新旧夹缝中的生存者,她的悲剧是注定的。
正如那个三等妓女翠喜。那些年,曹禺经常混迹于低层百姓之中,包括去妓院,“整个一个暑假,见过许多三等妓女,认真地参访这些人。人家也奇怪,干吗记这些话。我说我是报馆记者。”这种零距离,使剧作家不仅学会了谦卑,且发现了人性中沉潜的光辉。“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般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钱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
尽管前途一片惨淡,可为着一群老小,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对于生之痛苦,陈白露选择自杀做出最后的抉择。翠喜则恰恰相反,她没有死,不能死,必须痛苦的活着。正如曹禺在《谈悲剧》中所说,“悲剧的人物有一种美丽的、不为成败利害所左右的品德,悲剧的精神使人振奋,使人勇敢。”
在女儿万方看来,父亲将现实中的爱情与他对剧中人物的感情合二为一:“他爱女人,像干涸的泥土地需要水,他需要爱更需要付出爱,蘩漪、愫芳、陈白露,她们都是他的心尖儿,他珍爱她们,疼她们,多少男人里才有一个会这样地爱女人啊!这些女人已经进入了他的生命。”其实对曹禺来说,无论人的身份地位如何可怜、可笑甚至可悲,都应该有生存的最基本权利和尊严。伟大的戏剧家理当为这种权利和尊严而呐喊、呼号,多一点仁慈与怜悯,少一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傲慢与偏见、苛责与冷漠。这才是一个作家高贵的节操、格局和情怀。